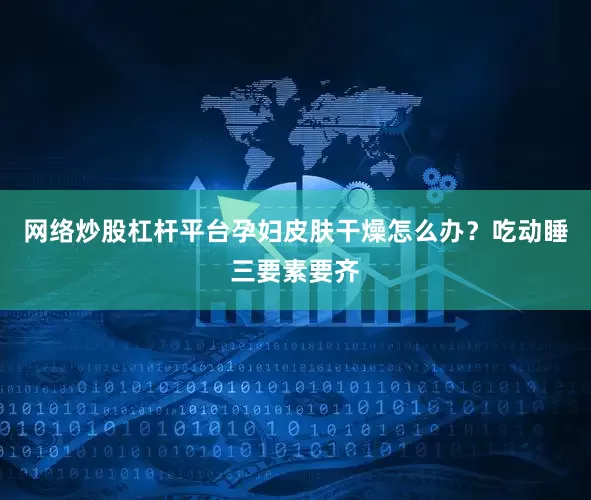上回说到嘉靖召“三路诸侯”进京开会,会议结果主要是两条:继续推行“改稻为桑”国策和赈灾。
这两项工作都要人去做,所以最重要的还是人事。
涉及的三方,内廷仍让杨金水江南织造局去,他以“不隐瞒”赢得了“忠诚”的考评;所以这一方不变。
严党方面,因为严嵩是首辅,严世蕃则管着吏部,人事方面是有主动权的。
被列入严党但事实上成了“独派”的胡宗宪原本任浙直总督兼浙江巡抚,属于军务民事双抓,现在免去了浙江巡抚一职,就是说主要工作是抓抗倭。
接任巡抚一职的是原浙江布政使郑泌昌,那么民事,说白了就是“改稻为桑”之事就主要是他负责了。布政使则由原按察使何茂才接任,跟郑泌昌穿一条裤子那位。

等于说,严家父子又把主动权抓在自己手上了。
这是浙江官场高层的变化。中层也要动,这是具体搞执行的岗位。
原杭州知府马宁远已经被砍头,派谁去?
严世蕃物色了一个人,这个人是他的门生,翰林院编修高翰文。
高翰文出身江苏望族,才华满腹,精通音律(却料不到正因此而吃了大苦头),自然也是满怀抱负,身在翰林院四年,心系天下,关注到浙江的事情后,他灵感大发,写了一篇题为《以改兼赈,两难自解》的文章。
严世蕃之所以看中他,正是因为看到了这篇文章,觉得派这个人去浙江保管没错,所以就破格提拔了他。
并且一破到底,特意在府中接待了高翰文,赠他以珍贵文房四宝,包括犀角笔杆、蓝田玉笔套、红毛黄鼠狼尾毫笔,还有宋墨、宋砚与李清照燕子笺,强调这不是让他写字的,是用来“传家”的。
罗龙文、鄢懋卿则不失时机地在旁烘托,强调小阁老对高翰文的“赏识”,当然也少不得提醒高翰文,可不能只收礼不干活,“一年之期大功告成,我们还等着你用这四宝写捷奏呢。”
高翰文是个感性的人,很是感动,当场跪誓“一年完不成改稻为桑,就用这套笔墨写自己祭文”。
他可不知道,浙江的情形跟他眼前所想完全不是一回事,他的豪情壮志很快就会被现实击碎,同时深刻认识到“说说容易做着难”的道理(这对他异日换赛道取得成功倒还是有好处的)。
严世蕃也会认识到,他用了高翰文,真是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”。
不过,至少眼前,严党从上到下都是信心满满。毕竟他们已经借此将亲信安插至浙江关键岗位,为兼并百姓土地打好基础了。
而裕王方面,看起来在用人方面是无法与严党抗衡了。
在人事布局被动的情况下,他们一开始想通过不给浙江拨粮(高拱管户部),让浙江彻底乱起来从而使严党陷入被动的方法打击严党。
就是说,为了党争,不必说严党,就连包括明朝首席政治家张居正在内的内阁清流一派(此时徐阶、高拱尚未到裕王府,但观点基本会一致)也是可以牺牲十多万百姓的。
裕王也这样觉得。
但是这样的方案被一个女人推翻了。她就是李妃。
李妃真是非同一般,正当几位大佬讨论之时,她抱着世子来了,裕王还不高兴,她却要裕王抱一抱世子,然后问他有几个儿子,裕王不耐烦地回答说就一个儿子,李妃说他的回答“又对又不对”,并且不管对还是不对,张居正他们的方案都不对。

从对的方面讲:
“我大明的江山社稷,王爷是皇储,接下来王爷手里抱着的世子是皇储。念在这一条,你们也得往远处想,要给王爷和世子留一个得民心的天下。”
从不对的方面讲:
“王爷是皇储,也就是将来的皇上,大明朝所有的百姓都是你的子民,将来还是世子的子民。哪有看着子民受难,君父却袖手旁观的!胡宗宪尚且知道爱惜自己任地的百姓,王爷,还有你们,难道连个胡宗宪也不如吗?”
还说:
“大明朝不是他们严家的大明朝,更不是他们底下那些贪官豪强的大明朝,他们可以鱼肉百姓,王爷,还有你们这些忠臣,你们不能视若无睹。”
真是对极了。政治站位比内阁大学士们都要高。张居正他们听了不仅肃然起敬,更是既惭且愧。
那难道就配合甚至帮着严党“两难自解”?
又是李妃看出了一个严党和清流都没有关注的“角落”:高层中层都被严党占了,但下层也就是淳安和建德两县却没有染指。
这两个七品芝麻官岗位,严党是不屑于刻意安排的,因为太基层了,对一县来说如天大,对上来说却根本没有什么话语权,上面叫做什么就照做,出了问题掉脑袋都属于陪斩。
上一任常伯熙和张之良就是这样的角色。
李妃却看到了一个机会。她提出这两个县可不可以派两个好官去。
裕王不以为然,说:“巡抚和管淳安建德的知府都是他们的人,争两个知县有用吗?”李妃却回答得干脆:“有用。”
这回不用她进行阐释,谭纶支持了李妃的观点,再怎么说,“直接管百姓的还是知县”,并且更进一步说,只是好官还不够,还须能“抗上”,“尤其是淳安这个知县,这个时候去,就得有一条准备,把命舍在那里”。
张居正显然也赞同,但也觉得难度太大,说“当今之世,这样的人难找”。
其实这样的人古往今来一直都难找啊。要不然,为什么独独留下一个海瑞的大名呢?
对了,这个最难找的知县,就选中了海瑞。推荐人是谭纶。
当时海瑞在福建南平县任教谕,写过一篇为民陈情的文章。谭纶非常赞赏,把整文章都背下来,他当场就背给裕王、张居正他们听,特别是文中“是以失田则无民,无民则亡国”两句,胡宗宪也在奏疏里引用过的。
张居正听了非常激动,跟裕王说“此人是把宝剑,有他去淳安,不说救斯民于水火,至少可以和严党那些人拼杀一阵”,裕王也立即想跟吏部去说,提拔海瑞去淳安。
不料谭纶却又说此事未必容易,因为“能升职肯定情愿”一事“在官场说得通,可在海瑞那里未必说得通”,因为海瑞“自己愿做的事谁也挡不住。自己不愿做的事升官可引诱不了他”。

当然,“现在这个情形,以他的志向,叫他去淳安他应该会慷慨赴之”,但有一个“孝”字,他越不过去。
据谭纶介绍,海瑞是海南琼州人,四岁便没了父亲,家贫,全靠母亲纺织佣工把他带大。中秀才、中举人,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,就是科场不顺,中不了进士,那份志气也便慢慢淡了。
现在把那颗心都用在孝养母亲上。都四十好几的人了,他一个月倒有二十几个夜间是伺候着老母睡在一室。”
海门三代单传,到现在还只生了一个女儿。因此,要是叫他此时任淳安知县,很有可能便是壮士一去,风萧水寒!无论是奉养老母,还是为海门添嗣续后,‘孝’之一道,他便都尽不了了。
有什么能够让海瑞有充足的理由离开母亲膝下慷慨赴任呢?得写信去说服他。
这个时候就需要张居正发挥作用了。大家知道张居正号称“神童”,写文章厉害无比,他们给海瑞的信里下面这几句真的很难拒绝:
“公夙有澄清天下之志,拯救万民之心。然公四十尚未仕,抱璧向隅,天下果无识和氏者乎?其苍天有意使大器成于今日乎?今淳安数十万生民于水火中望公如大旱之望云霓,如孤儿之望父母!
豺虎遍地,公之宝剑尚沉睡于鞘中,抑或宁断于猛兽之颈欤!公果殉国于浙,则公之母实为天下人之母!公之女实为天下人之女!孰云海门无后,公之香火,海门之姓字,必将绵延于庙堂而千秋万代不熄!”
这段话说下来,确实正气凛然又煽情,不仅让大家佩服,李妃也对张居正产生了一个女人对男人的仰慕之情。
这实际上也符合张居正的心境。多年后他作为内阁首辅,为了不使改革半途而废,就甘受天下物议而“夺情”。
这封信对海瑞来说更不用说了,可谓搔到了他的痒处,又激发了他的斗志。说实话,这些话如果让常伯熙张之良等寻常官吏看了,恐怕会视为忽悠的,但海瑞却是非常之人。
海瑞向母亲说明浙江灾情:严党为贱买土地,串通毁堤淹田,朝廷知情却纵容。

海母为此而震惊了,同时又明晰地感受到了一种危险:既然是朝里的忠臣写信给海瑞,调他去淳安当知县与严党争,可为什么“那么多大官不争,却叫一个知县去争”?
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。海瑞只能说,他并不清楚全部内情,但几十万百姓总得有人为他们说话,为他们做主。
他明知自己被挑中是因为他们认准他会为了百姓跟严党争,就算他们的出发点并不是百姓而是党争,他也会答应。
因为海瑞是真正把百姓放在心上的,只要是为民,哪怕他只是被利用一时的剑,甚至功未成剑已折,他也心甘情愿。
(网图侵删)
#大明王朝1566#
前十大证券公司排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配资利息计算公式一览表当你的见识超越大多数人时
- 下一篇:没有了